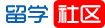就市容而言,美名远播的意大利名城米兰,除了模样古老、行驶得咣当咣当的有轨电车之外,在上海客眼里,实属乏善可陈,没有多少魅力。
论新,上海这些年盖了多少弹眼落睛的摩天楼,米兰有吗?虽然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就此被几何形体和现代光影取代或遮蔽。论老,光是外滩那一溜石楼,有几人说得清它们的建筑风格、前世今生?若非大气魄大规模的拆除,曾经的上海老建筑还是可以与米兰论论短长的。所以,上海客用得着千里迢迢跑到此地来崇洋媚外充内行装蒜吗?尽管米兰街头时不时不期而遇的雕塑、建筑立面和建筑细部,总让人产生在史与诗的密林中寻章摘句的恍惚。
街上随处可见的烟头杂屑,电线杆、配电箱等等器物上满头满脸的小广告“牛皮癣”,真叫改邪归正的上海客扬眉吐气。放肆的“国际统一面孔”的“涂鸦艺术”病,上海传染上的地区还真不多。高峰时,陈旧的地铁里一样前胸贴后背,但见纹身与ipad齐飞,美女与酷客辉映。至于路两边停满车辆有碍交通的状况,彼此彼此,扯平了。
不过,冲着马克·吐温“大理石诗”的比喻,杜奥莫大教堂是不可不去的。顶含135座尖塔、3159尊雕像的大教堂,上半部采用哥特式,下半部却是巴洛克式——时尚之都的米兰人,早在1386年,已经玩起了混搭。 整座教堂全用大理石砌筑,足以叫暴发户惊叹。墙壁、门窗、柱垛……上的雕刻,应从传神角度欣赏,不应以精细评论,那可是暴发户理解不了的。抬头望见尖塔林,心中想起劳伦斯。“刺猬式大教堂”的比喻,可谓绝妙。我正欲肃立致敬,却瞥见堂而皇之高挂教堂壁上的巨幅商业广告。
杜奥莫广场成百上千的鸽子自由而飞自在而落,毫无避忌地在开国君主艾玛努埃莱二世的肩头和帽盔上歇脚。我欲将人类与鸟类亲密无间的和谐情景收入镜中,鼻前蓦地伸进一只乌黑的手,手托一把金色玉米。记得朋友的预警:接受这把鸟食意味着50欧的代价。
倘佯,不断与知名或不知名的雕像打招呼。一处小而杂乱的街心绿地里居然也竖了一块高而扁的碑。从扭曲的人体浮雕与碑上刻写的年份来看,估摸与二战有关。碑前供着松果与干花编扎的花环。环上三色绸带有七八成新,敬献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。为何碑立此地?为何至今供花环?莫非此地与墨索里尼有关?走进一边的楼里找人询问。被问者或混然不知墨索里尼何许人也,或语焉不详,或鄙夷不屑……终于有白须老者告之,墨索里尼当年的办公室正在这楼里。而如今,这楼早已是商务楼了。
风起云聚,骤雨袭来。躲进咖啡馆,透过落地大玻璃窗看湿漉漉拼成波形图案的碎石路上色彩斑斓。不久雨歇,快九点了,远近建筑物顶部罩上几块金黄色夕阳柔光。我想,那大教堂现在一定成了剪影,剪影后蓝灰色云层一定有着瑰丽裂隙。我的思绪由夕照跳回灿烂阳光下纪念碑扭曲的人体和花环上。
我想,刽子手墨索里尼是被鄙夷了被遗忘了,而受难大众没有被忘记。是,怎可忘记大众的苦难?我仰脖一口喝干咖啡——在意大利天天喝好多很苦很香的浓缩咖啡——这一杯却不苦,只有香。(出国留学网 liuxue86.com)